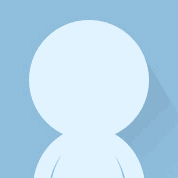绍兴的水乡在傍晚时分安静得出奇。乌篷船停靠在岸边,河面漾着一层薄雾,石桥的倒影被波纹切碎。小巷狭长,青石板湿润,墙角苔藓泛着深绿。段元诚沿着小巷走着,鞋底的声响被水气包裹,显得格外轻。他的身旁,是拎着木匣子的吕先生。

吕先生是篆刻师,木匣里装着刻刀与石章。他走路很慢,偶尔停下来,抬头望一望檐角的花纹,或是摸一摸桥栏的石纹,就像要把眼前的事物“先收录进手里”。
他们走进一间废弃的老祠堂。大门早已斑驳,梁上吊着的木牌隐约还能辨出“敦宗守礼”四个字。屋内空空荡荡,只剩下几支残破的柱子支撑着。风穿堂而过,带动尘埃在暮色里旋转。
段元诚环顾四周,随手在笔记本里写下一句:“这是某个家族最后的影子。”吕先生却没有立刻动笔,而是坐在石阶上,打开木匣子,取出一块温润的寿山石。他将石头放在手心掂了掂,拿起刻刀,缓缓刻下几个字。
刀与石摩擦,发出极轻的声响,在空旷的祠堂里却显得清晰。段元诚看见,吕先生刻下的并不是大字,而是小而细的篆体,只有凑近才能看清——“见证”。他没有解释,但这两个字足以概括他们此刻的存在。
夜色渐深,祠堂外的河水映出点点灯光。远处传来船夫的歌声,混着橹声敲击水面的节奏。吕先生刻完,把石章轻轻吹去碎屑,在纸上拓下一枚印迹。那鲜红的印章在昏暗里格外醒目,就像被时间按下的一枚坐标。
“石头会留,字会留,祠堂未必留。”吕先生轻声说,语气里没有遗憾,更多的是一种平静的确认。段元诚把这句话记下,心里觉得,这才是他们存在的意义——不是去挽救,而是去证明。
离开祠堂时,夜色已经完全罩下。青石板路上只有他们的脚步声。河对岸有人在点灯笼,橘黄的光被风吹得摇曳,倒映在河里,就像一行断断续续的诗。
段元诚回头看那座祠堂,黑暗中几乎看不见轮廓,只有方才印在纸上的那一枚红章,像是它最后的呼吸,被留存下来。
他们并肩走进小巷深处,吕先生把木匣子抱在怀里,神情安静。段元诚想,也许这座城市的未来未必能记住一栋祠堂,但会记住某一枚篆刻、某一行文字,以及当时有两个人曾在这里停步过。